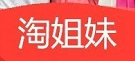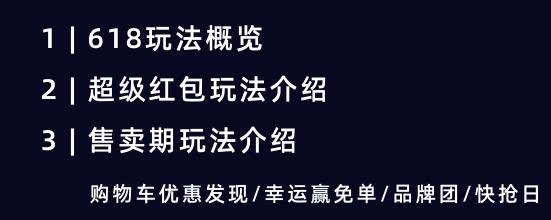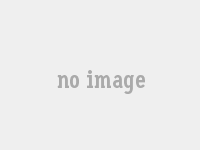年轻少妇过着寡味的日子,却偶遇旧时情人,《小城之春》爱恨纠葛
淘宝搜:【天降红包889】领超级红包,京东搜:【天降红包889】
淘宝互助,淘宝618微信互助群关注公众号 【淘姐妹】
费穆与抒情中国
从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情绪是“不合时宜”的,纵观这些影片的评价,除了《城市之夜》《狼山喋血记》在意识上是“进步”的,其他影片都不可避免地被贴上“布尔乔亚”或逃避主义的标签。
显然,时代的脚步已不可阻挡,那么停下脚步的人自然落伍了,而费穆某个层面来说便成了没有往前走的一员。
《小城之春》上映后,有评论贬斥:“现在已不是使人性、个性、愤怒、痛苦的压抑时代,而是爆发、呐喊的日子,费穆先生的才华经验在压抑手法下,阻碍了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费穆是寂寞的。
正如费穆之女费明仪谈及父亲在去世前夜说的话:“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寂寞,问题是我的感受,究竟有多少人能了解?!”面对时代之潮的不可阻挡,费穆从“情”中寻找出口,《小城之春》在现实主义的潮流中,以抒情的气质独树一帜,呈现了另一重中国的模样。
战后时期,费穆有两部影片《生死恨》和《小城之春》,其中前者践行了他一以贯之的“旧剧电影化”理念,后者则讲述了一个关于“苦闷”的故事。费穆指出《小城之春》欲传达“古老中国的灰*绪”,在无技巧的手法下影片以一种别致抒情的“费穆风”打动着观众。
王德威认为费穆的电影美学与中国的抒情传统密不可分,“电影,对费穆而言不单纯只是‘承载’写实主义,或是‘展现’情感,它更创造了诗意抒情的觉醒”。
黄爱玲则指出费穆的电影艺术在“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这种“中国性”指来自传统文化和戏曲艺术的诗意感,而诗意的营造则属于抒情的逻辑。
抒情的距离:剧作的三重意义
须知,《小城之春》中署名的编剧并不是费穆,而是当时的影坛新人李天济。1947年,时年26岁的李天济写作个人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小城之春》,在剧本不被赏识的情况下,费穆看中了它,便有了后来的《小城之春》,剧作的底色正来自此。
据李天济回忆,费穆在第一次见到他时吟诵了苏东坡的《蝶恋花》,所谓“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一语道出《小城之春》的抒情之旨。从剧本原来的名字《苦恋》和《迷失的爱情》来看,“情”是贯穿整个剧作的核心。
在被问起对剧本的看法时,李天济坦言自己曾和剧中人物有过相似的经历,无论是挚友间的微妙情谊抑或爱情里的生死纠缠,他都曾经历过,剧本的创作是以这种经验为基础创作的。有兴味的是,李天济在剧本中要传达的寓意并非止步于“爱情”之苦,而是一种“苦闷”的情绪。
他指出:“当时写剧本时,我不正是处于左冲右突,苦无出路的困境之中吗?”如此,《小城之春》的基调形成了。反过来,将《小城之春》的剧作归于李天济一人之功实在是偏颇的,换言之,《小城之春》剧作中的第二重意义来自费穆。
费穆对电影剧本是有要求的,正是这样的反思才有了后来和《小城之春》的相遇。《小城之春》上映后,面对褒贬不一的评论,费穆谦虚地回应:“假如《小城之春》有好的地方,是剧作者之赐,弄糟它的是我作为导演者之罪。”
足见费穆对剧本的重视程度。李天济曾撰文《三次受教倏然永诀》描述他与费穆的三次见面,而这三次见面都是一个主题――改剧本。费穆对《小城之春》的修改是将剧本趋向电影化的过程。
如果说李天济的原作底色和费穆的修改基于有形的文字介质,那么《小城之春》在剧作上的第三重意义则见于影片拍摄期间的即兴修改。早在国产电影的萌芽年代,被文明戏浸染的电影对即兴创作并不陌生。
在没有正式剧本的条件下,某种意义来说是即兴的表演孕育了电影剧作。有趣的是,《小城之春》的剧本几经修改和完善,费穆在拍摄期间却使剧本消失了。另一主演张鸿眉的回忆更有借鉴意义。
饰演妹妹的张鸿眉谈及费穆教她演戏的情景时说导演请她“忘掉剧本”,而忘掉剧本便是创作角色的开始。影片中妹妹有两场唱歌的戏,费穆请张鸿眉自己选歌曲,《可爱的玫瑰花》《在那遥远的地方》正是即兴的产物。
《小城之春》并非费穆即兴创作的开始,而是其创作习惯和创作规律的延伸。柯灵曾指出费穆在舞台剧创作上有一个特点“很少在事前写好剧本”,像《浮生六记》《红尘》的编排都是在没有现成剧本的前提下完成编排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剧本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剧作的消失,有评论指出影片在编剧工作上“运用了超脱的笔调,以抒情的氛围,把整个剧情轻描淡写得宛若一篇飘然的散文”,在导演层面以“精湛的抒情手法”营造出“恬静,淡淡的气氛”。
抒情的氛围作为影片的“空气”,从李天济几经易稿的剧本《小城之春》到费穆改写的剧本《小城之春》,再到银幕上的《小城之春》,三者在剧作层面显然是有距离的,这距离便成就了影片的抒情性。
抒情中国的生成
还是要从“古老中国的灰*绪”说起。《小城之春》上映后,杨纪发表了影评文章《〈小城之春〉试评》,不久费穆撰文《导演・剧作者》作为回应,这篇回应尽管只有寥寥数百字,却道尽其于《小城之春》的良苦用心。
一如影片的“无技巧”,这篇文章亦不事技巧,至情至性。费穆称长镜头和慢动作的使用意在传达“古老中国的灰*绪”,这种“情绪”不仅是《小城之春》的核心,在他的整个电影创作中也是始终一贯的。
曾有人评论:“费穆的气质太沉重忧郁,所关切的问题太博大深远。”这样的评论实际上倒恰好与费穆原要传达的主旨一致了。费穆在之前的《天伦》《孔夫子》中,个人化书写已非常突出,“古老中国的情绪”也是浸染其间的。
即便如《城市之夜》《狼山喋血记》等看似迎时代而创作的影片,也或多或少传达出这种情绪。《小城之春》的出现,则是这种情绪的集大成者。
巧妙的是,费穆在营造这一灰*绪的过程中,没有将它直接给予观众,而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完成的,被爱情装置后的古老中国少了些许沉重,多了几分哀愁,有如一篇诗歌或散文,散发出淡淡的哀愁。
与同时期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相对照,《小城之春》确实太特别,无论从人物设置还是剧情故事来看,似乎都与现实无涉,更谈不上控诉。除了“改良中国”“革命中国”外,费穆的中国叙述是抒情的模样。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1950年代发表了《现代中国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出发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浓郁的抒情精神,为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王德威将抒情传统扩展至抒情主义的视野中去讨论,他认为,费穆的影片创造了“诗意抒情的觉醒”,“拍出诗人捕捉人间吉光片羽的感悟”,而这正是“真正的‘中国’电影主体和诗心所在”。
作为电影剧作的参与者,李天济欲表达的是“苦闷”,费穆则引申为“古老中国的灰*绪”,前者指向个人层面,后者指向厚重家国层面,联结起影片的主要情绪。由此,《小城之春》剧作的抒情性分为指涉“个人”“家国”的两个面向。
《小城之春》的经典性有多个体现,其中旁白是被津津乐道的妙辞。从剧作的角度来说,旁白的运用呈现出“个人”这一面向的抒情性。
值得关注的是,影片不仅使用了旁白,且说旁白的人是女主角周玉纹,玉纹的全知视点打破了人物之间本身的限制,成为整个剧作中的中心,担任着替他人“发言”的角色。在这一条件下,当玉纹的内心独白出现时,便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心里叙事机制。
故事的开始,一段内心独白伴随着玉纹响起:“住在一个小城里面,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晨买完了菜,总喜欢到城墙走一趟,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不见、心不想。要不是菜篮拿着先生生病吃的药,就整天不回家了。”
这段惆怅的语言奠定了整部剧作的“灰*绪”基调,而故事中的每个人物也是通过玉纹的旁白和画面完成出场的。有趣之处在于,玉纹的全知功能在章志忱出现后被消解。“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
“他居然叫礼言,我不知道礼言也是他的朋友。”如果说整部剧作都采用全知视点进行叙事,观众的观影经验也是全知的,但是当玉纹的这一叙事功能失去时,观众也会随之进入叙事的有限。
与此同时,玉纹的旁白、独白在全知和非全知的视点中是经常转换的。尽管费穆称影片是“无技巧”的,然而这种讲述故事的“无技巧”显然是刻意为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视点的转换自如营造了若即若离的诗意和抒情。
台词也是要特别指出的,“无技巧”作为影片在架构时的原则,台词是相当精简过的。妙的是,抒情的氛围恰在这些寥寥数语中形成的。
如在城墙上,志忱和玉纹并肩靠着,志忱问:“假如我现在叫你跟我一块儿走,你也说随便我吗?”玉纹看着志忱:“真的吗?”你来我往间凸显了二人的情欲角力。
结语
回到费穆临终前的那个夜晚,他对女儿说:“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寂寞,问题是我的感受,究竟有多少人能了解?!”费穆是超越时代眼界的,大约抒情是试着理解他的一把钥匙,更好地理解那个“背着十字架”[28]对时代潮流始终保持着距离的电影诗人。
参考文献
[1]费明仪:《序》,黄爱玲编《诗人导演费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尘无:《最近的中国电影》,《旁观者》,1934年创刊号。
[3]安娥:《看了〈小城之春〉》,《远风》,1948年第3卷第1期。
[4]费穆:《导演・剧作者》,《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9日,第8版。
[5]余爱渌:《小城之春》,《前线日报》,1948年8月2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