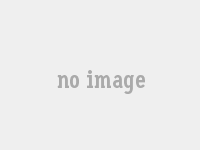游客与跟团游是如何发明出来的?
淘宝搜:【天降红包222】领超级红包,京东搜:【天降红包222】
淘宝互助,淘宝双11微信互助群关注公众号 【淘姐妹】
19世纪中期后不久,随着图像革命开启,出国旅行的特性――首先是欧洲人的旅行,然后是美国人的旅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在我们的时代达到高潮。在此之前,旅行需要长时间筹划,花费极巨,耗时极长。旅行可能威胁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旅行者曾是主动的,现在他变得被动了。旅行不再是体育锻炼,而成了观赏运动。
这一变化可以用一个词描述。这是旅行者的衰落,游客的崛起。这些词语有着妙极了的准确性,但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旧英语名词travel(就其旅行的意义)原本和travail(意为“问题”“劳作”或“折磨”)是同一个词。而travail一词,应该是通过法语作为中介,从通俗拉丁语或罗曼语族中的trepalium转化而来,指的是一种三足的折磨用刑具。去旅行――去travail,或(后来的)去travel――在当时就是一种劳神费力、十分麻烦的经历。旅行者是个积极忙碌的人。
在19世纪早期,一个新的单词进入了英语,我们得以从中窥见旅行的世界经历了什么变化,尤其是在美国人眼中。这个词是tourist(游客)――刚开始中间还有个连接符,写成tour-ist。我们的美国词典现在把游客定义为“一个愉快旅行的人”或是“一个旅行的人,尤其是为了享受而旅行的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tourist一词中的tour是使用逆序构词法从拉丁词tornus而来的,而这个拉丁词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一种画圆的工具。这样一来,旅行者是在从事某项工作;而现代游客则是找乐子的人。旅行者是主动的;他费力去寻找人、寻找冒险、寻找经历。游客是被动的;他期待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去“观光”(sightseeing,这个词也在同一时期出现,最早的成文记录在1847年)。他期待一切都替他料理好,为他服务。
出国旅行不再是一种活动了――一次经历、一个任务――而是一种商品。游客的崛起起初只是一种可能性,后来成了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吸引人的旅行项目被包装起来,以套餐出售(所谓的“包价游”)。通过购买一次出游,你可以强制另一个人保证有趣并宜人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以批发(长达一月或一周的旅行,或某国深度游),也可以零售(一日游,或是只参观某个外国首都)。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我们十分熟悉,在此也有必要再提一次。首先,最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交通的进步。19世纪后半叶,铁路和远洋轮船真正把旅行变得舒适了,不适应风险突然减少。整个历史上,长途运输工具第一次得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能够卖给许多人,还十分廉价。为了保证能得到满意的投资回报,它必须要大量卖出。在任何一种旧交通方式上投入的资本――从公共马车到航船客舱――都远远比不上铁路(即使只是一节卧铺车)或豪华游轮的投资。这些资本投资之庞大,意味着必须要让设备时刻运转,运送成千上万的旅客。现在,一大批人将会被引诱出门,为了享乐而旅行。庞大的跨洋轮船只靠外交官、出公差的人或像亨利・亚当斯这样为提升教养的人可填不满。消费群体必须扩大,包括出门度假的中产阶级,至少也要拉上上层中产阶级。出国旅行被大众化了。
显而易见的下一步就是“跟团游”。计划完备的团体出游甚至能把爱待在家的害羞者吸引出来。当然,由导游带领的旅行十分古老:十字军东征有时候也和这有些相似。我们可以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看到,在14世纪后期,塔巴德酒馆那博学慷慨的主人就提出:
但在那之后,少有向导免费提供服务,向导引领的旅行本身成了一种商品。冒险被打包成套餐出售,保证消费途中没有风险。在英国,旅行距离很短,中产阶级兴盛,铁路发展得早,因此催生出第一次组团旅游。根据传说,第一个旅游团出现在1838年,火车将游客从韦德布里奇带到邻近的柏德明,在那里参观两个杀人犯的绞刑仪式。由于柏德明行刑的惨状在露天车站就能看见,这些短途游客甚至没走下开放车厢就享受了这场乐子。
创造并推广跟团游的真正先锋自然是托马斯・库克。他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安排英国国内的特价火车游。他筹备的第一次团体游把将近六百人从莱斯特送到相距十八公里的拉夫伯勒,花费很低――打折后的双程三等车费,每人只要一先令。很快,库克就把上百人送往苏格兰(1846)和爱尔兰(1848),在1851年,他更是把上千跟团游客送到了伦敦水晶宫博览会。1856年,他打广告宣传其第一次“环欧洲大陆大型游”,游览目的地包括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滑铁卢战场、科隆、莱茵河及其两岸、美因兹、法兰克福、海德堡、巴登C巴登、斯特拉斯堡、巴黎、勒阿弗尔,然后回到伦敦。而后,在他极富创业精神的儿子的帮助下,他还推出了瑞士游、美国游,最后在1869年,便是第一次中产阶级向耶路撒冷的东行。他很快就开发了一系列便利服务:彬彬有礼、知识丰富的导游,酒店打折券,订房服务,防止疾病和偷窃的保护及建议。
精致的英国人对此很是抗拒。他们说,库克是在剥夺旅行者的动力、夺走他们的冒险,在欧洲大陆的风景里塞满没教养的中产阶级。“坐火车去,”约翰・罗斯金抱怨道,“我觉得根本不能算作旅行;这不过是被‘送’到一个地方,就跟货物包裹没什么两样。”《布莱克伍德》杂志在1865年2月刊发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驻意大利领事,他对此大加攻击,称“这种新出现的邪恶行为正不断增长……把四五十个人,不顾性别年龄混在一起,从伦敦送到那不勒斯再接回来,收取固定费用”。“意大利的城市,”他哀叹道,“被这一群群生物塞满了,因为他们从来不分开行动,你会看见他们四十多人聚在一起,跟着导游沿街道乱走――一时在前,一时在后,到处打转,像牧羊犬一样――真的,这景象与牧羊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很小了。我已经碰见了三堆人,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粗野的东西,里面的男人大多年纪不小,很沉闷,怏怏不乐;至于女人,年纪稍轻些,舟车劳顿,但活泼得不行,很是精神,轻浮不已。”
库克为他的服务辩护,他把这些旅行叫作“促进人类进步的手段”。他说对这些旅行的攻击完全是在摆架子,这些批评者都是老古董了。“认为罕见而有趣的地方不该由普通人享受,而应该只为‘特选’社会成员的利益服务,这多么愚蠢。但在这个进步的年代,再说些什么特权的胡话太不合时宜了,上帝把地球造得这样充实而美丽,都是为了人民;铁路和蒸汽船是科学一视同仁的光辉所带来的产物,也是为人民而存在的……最优秀的人,最高贵的思想,看见人民跟随他们的脚步,领略他们领略过的乐趣,只会欢呼雀跃。”
然而,在美国,虽然所有人都突然负担得起这一切了,运送移民还是比运送旅客有利可图多了。往来奔波、塞满了移民的初期美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看不出旅行有多少光彩。在美国人看来,出国旅行很大程度上仍是贵族的专属,这种想法甚至比英国人持续得更久。直到20世纪早期,想跟团游览欧洲的美国人还要依赖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格兰特总统就用过库克的服务。马克・吐温对库克这种全新的、无忧无虑的傻瓜式旅行商品做了最好的描述:
库克把旅行变得很简单,成了一种享受。他会卖给你一张票,把你送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所有地方,给你所需的所有时间,他所提供的远远不止于此。他为你提供任何地方的酒店,完全随你心愿;你也不会被索要过高价钱,因为打折券上标明了你具体要交多少钱。库克在大站台的员工会照料你的行李,为你叫出租车,告诉你要给司机和搬运工多少钱,帮你找来向导、马、驴子、骆驼、自行车或是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让你的日子过得舒服又满意。库克随时随地为你提供银行服务,若你不慎被风雨困住,他的产业也会为你遮风挡雨。他的文员会回答你的所有问题,而且答得彬彬有礼。我建议您旅行时买库克的票;我堂堂正正地提出这个建议,因为我没有拿他一分钱。我并不认识库克。
库克公司一直保持着早期建立的领导地位。它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旅行社。
该公司在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美国运通公司。它的前身是著名的威尔斯公司、法戈公司再加上其他公司,19世纪中期这些公司在美国国土上运输货物和金钱。19世纪,这些中介从流入美国的移民潮中获取了不少利益,它们负责为成功的、刚到美国的美国人给在欧洲急需金钱的家人汇款。1891年,第一张美国运通旅行支票获得版权,其后,这个发明为旅行者解决了许多担忧。(到1960年,每年的销售额达到二十亿美元。)1895年,美国运通在欧洲开设了第一间办公室。刚开始,该公司向美国旅行者提供的服务只包括邮寄信件、订火车票和预订酒店,并帮忙找回丢失的行李。执掌公司直到1914年的詹姆斯・C.法戈总裁坚持认为旅游业没有利润。他说,美国运通应该专注于货运和快运。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加强的各快运业务无可避免地改变了市场格局。即使在一战结束前,美国运通就已经在发展大规模旅游服务,战后,公司的旅游部门大幅发展。到1961年,美国运通所服务的客户已遍及全球,在全世界共有二百七十九家办事处。
美国运通战后组织的第一个欧洲旅游团在1919年10月出发。其后不久,第一个地中海团就乘着冠达航运公司的“卡罗尼亚号”出发,该船由美国运通和库克公司共同控制。1922年,美国运通开启第一次海上游轮环游世界之旅,使用的轮船是“拉科尼亚号”。在这之后,每年都规划了一次相似的游轮旅行。大反击开始了。美国人返回旧世界,发起巨大的旅客冲击,其强度随着美国的财富上下波动,但近年来,冲击的强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到20世纪中期,出国旅行成了一门大生意。它是美国生活标准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我们与世界其余地区文化与金融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1957年,约一千万美国居民在国际旅行上花费超过二十亿美金。在这些旅客中,有一百五十万人跨洋旅行。仅在1961年夏季,估计就约有八十万美国人到欧洲旅游,在当地消费约七亿美元。
出国旅行现在当然成了一种商品。就像任何其他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一样,它可以用批发价购买,还可以分期付款。19世纪早期,波士顿的查尔斯・萨姆纳向几位相信他未来会有出息的老朋友借钱去欧洲旅游,当时这被看作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奇特事件,一件咄咄怪事。现在,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在付不起旅费的情况下出游。“现在先去,日后再给钱。”你的旅行社会帮你安排的。
当旅行再也不是量身定做,而是流水线产物、可以在店里买到时,对它的内容我们就没那么多可说的了。我们也越来越不清楚我们买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购买了若干天的假期享受,甚至也不知道套餐里包含什么。最近在周游讲学时,我乘飞机到了海得拉巴――一座位于印度中心的城市,这名字一年前我甚至连听都没听过。飞机上,邻座是一个疲惫的美国老人和他的妻子,他是从布鲁克林来的房产经纪。我问他,海得拉巴有什么好玩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夫妇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个城市“在套餐里”。他们的旅行社保证,套餐里只会有“全球闻名”的目的地,所以这城市在世界上肯定大有名气。
一个好的旅行套餐必须包含保险。在这个意义上,旅行的危险性成了过去式;我们买的套餐直接包含安全和内心的平静。别人帮我们把风险都担了下来。1954年,悬疑片《情天未了缘》描绘了一架豪华班机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一次问题重重的航行。机上各式各样的度假者乘飞机前往中太平洋,享受一到两周的悠闲假期。引擎熄火后,乘客的精神开始崩溃。最后,为了让飞机不至于坠毁,机长要求把行李扔下去。我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座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母子,孩子还很小。他看上去不太纠结于乘客所面临的生死危机,但当乘务长把乘客各种雅致的随身行李扔进海里时――奢华行李箱、帽盒、便携打字机、高尔夫球杆、网球拍――男孩开始坐立不安。“他们怎么办啊?”男孩大喊道。“别担心。”母亲安慰他,“都上了保险了。”
当旅行者的风险由保险承担时,他就成了游客。
责任编辑:赵思远
海拔最高边境检查站的守卫者:最冷零下40℃,总去无人区救援,“如果真的走,会争取最后一批离开”
海拔最高的边防,边境检查站级别,边境检查站视频,海拔最高的边防哨所西藏日喀则和阿里的分界线上,坐落着马攸桥边境检查站。它是阿里的南大门,也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边境检查站――海拔4960米,方圆100多公里都是无人区。
检查站在两道山坡的中间,一侧的山坡爬满了骆驼刺,另一侧只有晒得发白的裸露山岩,云朵厚重得像雪山顶,219国道横贯而过。
37岁的王宇是马攸桥的移民警察,个子瘦瘦的,脸上带着日晒留下的黑斑,笑起来门牙间有一条缝。因为常年在高原生活,他的眼球微凸,布满红血丝,风沙使得泪腺堵塞,眼眶里常带泪水。
王宇。图/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在马攸桥工作的13年间,他参与了200多次救援和100多次牧区义诊。得知牧民没有防护用具,他自费给牧民买了50多副墨镜和40多双棉鞋。
2019年,出于对高海拔戍边警察的关怀,王宇被调去西藏海拔最低的地方――海拔680米的背崩边境派出所。一年后,他写了返调申请书,重新回到这片氧气稀薄的地方。
在申请书中,他写道:“犹记得,一个个前来求助游客焦急变成感激的眼神,同志们朝夕相处、大家庭的温馨,巡逻检查的使命感和光荣感。我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坚守,在每个清晨和黄昏守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那里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一样。”
今年7月,西藏边检总站实行高低海拔轮换,9名警察调离马攸桥。
“这地方怪得很,没来的不想来,来了的不想走。”王宇不在第一批轮换的名单里。但三年内,多数民警将要去往下一站。
现在,他必须再次适应将来与马攸桥的离别。
【1】无人区
2010年初到马攸桥时,王宇觉得“四周光秃秃的,很荒凉,刚来就想走”。
马攸桥边境检查站建于2003年,至今仍是西藏唯一一个没有通电的边境检查站,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和太阳能发电。到了晚上,电力要供给岗亭的执勤工作,营房宿舍里,常常是黑黢黢的,不亮灯,插板也全部停电。
那时检查站没有电动检查杆,杆子就只能拿石头压住,没有电脑,只能手写登记。营房常常漏雨,电话经常没信号。快递最快要15天,慢的要走一个月。有一回,单位有家属寄来烤鸭,抽了真空袋,快递到时,鸭子都泛了酸味。
马攸桥边境检查站。图/九派新闻记者 肖洁
这里是无人区。因为常年缺氧,副站长赵玉龙指甲发紫,指尖呈紫黑色,嘴唇堆着干裂的皮屑,风沙在脸颊刻下粗粝的纹路。即便在高原工作多年,他们的血氧值仍不到80。
王宇是单位的卫生员和种植员。因为小时候跟着家人种过蔬菜,他在单位管了10年蔬菜大棚。温室里种了黄瓜、西瓜,绿色浓郁,有时他会采摘一些,送给牧民和游客。在军营里,一个最为经典的笑话是,“当兵三年见不到绿色,回家后抱着树哭”。
附近没有理发店,单位买了理发工具,理发时只能互相帮忙。唐勇军休假回家,跟着开理发店的妻子偷学。回马攸桥后,他成了队里的“理发师”。
刘伟和王金东负责看管和维护发电机。由于只有两台50千瓦的发电机,刘伟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加油。这里风沙大,机油容易进杂质,发电机常常故障,刘伟和王金东只能错开休假。调走前,他们还得带出一个会修发电机的徒弟。
冬季漫长。10月飘雪,5月融化。全年平均气温为零下11℃,最冷零下40℃。每年有3到4个月时间,水管会结冰,需要用开水烫1个小时才能抽水。
巡逻或开车或徒步。车巡无法观察到的细节,需要登上马攸木拉达坂的高点,用望远镜观察周围是否有人绕关过卡,有没有遇险人员。达坂的雪多时有1米厚。那里是事故频发的地方。
冬季,马攸桥边境检查站的民警们巡逻。图/受访者提供
站在5211米的“马攸木拉山”标志牌旁俯瞰山底,王宇有时能看到一半黄土坡,一半冰雪层。回来时,他的眉毛和睫毛会结一层霜。在零下40℃的天气里,他的手指变得弯曲、僵硬。他的脸也起了一层硬壳,像动物蜕皮前的样子。
【2】救援
马攸桥边境检查站驻守在马攸木拉山下,守卫着阿里地区的“南大门”,是沿219国道进入阿里的第一道关卡,担负着进出阿里地区人员、车辆、物品查缉以及救灾救援等任务。
过关卡时,马攸桥的移民管理警察们会给群众发放一张警*系卡,上面写着民警的联系方式,“在无人区如果他们需要救援的话,一下就能联系到我们。”
这里的民警平均年龄30岁,最小的是00后。2019年1月,随着部队整体转隶,他们从边防*转改为国家移民管理警察。“只是换了衣服,职责没有变化。”
民警们身上还留着部队的习惯:头发是清一色的“板寸”,工作时间长的人,都被叫作“老兵”“老杆子”。
王宇的哥哥是一名戍边军人,5个堂兄弟也当过兵。在他儿时的印象里,军人高大神圣。2005年,王宇入伍,新训后分到阿里札达县,待了四年。第一年,暴雨冲塌了札达的一个水库堤坝,部队迅速集结,王宇一趟趟地往返运送沙袋,堵住水库的缺口。他第一次体会到军人的使命感。
2007年,王宇申请去做一名卫生员。马攸桥海拔高,高寒缺氧,即便是一个小感冒,若得不到及时治疗,都会引发高原肺水肿等急性病。
这里最近的医院距离约200公里,驾车需3个小时。因为周边大部分都是牧区,牧民生病也会来找警察。有时,王宇会和同事去牧区义诊。牧民们多有相似的病症:干眼症、慢性胃炎、高血压、高血脂、胆囊炎等,因为放牧时没带任何防护用具,不少人称眼睛疼。
2017年6月的一个晚上,一位牧民家的孩子发高烧到39度,父亲来检查站求助。王宇急忙带药赶去,等孩子体温恢复正常,凌晨4点才返回。后来几日,他每天前往牧民家,观察病况,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为了感谢,牧民悄悄将一只羊拴在营门旁边。他发现后,又将羊送了回去。
王宇说,因为曾目睹生命的逝去,所以对生命尤为敬重。有次,一对一岁左右的双胞胎坐大巴前往阿里,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一个孩子没了心跳。当家属求助民警时,王宇发现另一名孩子仍有呼吸,但频率不正常,他赶紧用上制氧机,做了急救措施,最终挽救了生命。
为了帮助牧民,王宇自费购买了50多幅太阳眼镜和40多双棉鞋。他在马攸桥还有一家帮扶对象。那户人家住在帐篷里,铺了大地铺,有一个藏式的小柜子和一张小床。他们家的大女儿16岁,患有软骨症,只能瘫坐在角落里。王宇自费给他们的大女儿买了出行用的小推车,衣服也买了七八套。一有空时,就带去大米、奶粉和罐头。
民警为牧民送去棉鞋和墨镜,右三为王宇。图/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今年4月,王宇将疫情防控点改造成救助点,免费为路过的骑行者提供床铺、热水、氧气瓶、纸巾等。改造以来,他自费购买了五次纸巾和氧气瓶,花费七八百元。最多一次,他救助了29名老人。
在马攸桥,王宇共参与了200多次紧急救援。说到印象最深的救援,他说,是一场长达8小时的救援。
2022年2月27日晚上8点多,他们接到报警,马攸木拉达坂有大量车辆被困。“路上的雪大约有70公分厚,没过了小腿”。为了抢占时间,民警们徒手用铁锹铲雪,用钢丝牵引绳拉出被困车辆。一个半小时后,被困车辆被救出。但雪越下越大,“风吹来的都是雪”。积雪最厚时达到了90公分,困住了往来的17辆车。
凌晨1点,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王宇和同事们通知交通部队后,坚持在大雪中指挥车辆,并为铲雪车开路。凌晨4点,道路恢复如常,所有车辆安全驶出了危险区域。
民警救援被困车辆。图/受访者提供
【3】归属
检查站里,一半的人都结了婚。但很少有家属会来马攸桥短住。这里路途遥远,需要长时间坐车,容易产生高原反应。
王宇和妻子是相亲认识的。她比王宇小8岁,性格内敛,是一名护士,孝顺善良。以前,王宇也相过几回亲,但对方大多都介意长期分居。王宇觉得,妻子不太一样,他分享自己在边境的照片时,妻子眼睛亮晶晶的,认为王宇“心好”,在做一份很有价值的工作。
2020年1月2日,考虑到王宇常年待在高海拔地区,身体出现很多问题,他被组织调去了林芝背崩边境派出所。接到通知的那一夜,他一夜未眠。林芝海拔仅680米,被称为“藏南谷地”,产菠萝蜜,有大片的绿色森林。但他高兴不起来,干什么都没有活力,提不起劲,也没有价值感。在背崩的日子里,马攸桥常常出现在他梦里。
因为妻子怀着孕,王宇没和妻子说起自己的烦恼。后来妻子得知,选择支持他,她说,“家里面不要担心,人在哪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在背崩边境派出所时,他读了《自卑与超越》。他想到,来马攸桥后,他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也疗愈了自己。马攸桥让他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我理解了自己,而且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他目光坚定。
王宇背后是大片的无人区。图/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2021年4月,王宇写下了返调申请,在信中,他写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那里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一样。”
王宇给女儿的小名取作“悠悠”,因为马攸木拉山的藏语是母亲的恩惠,“希望她能得到马攸木拉山的庇护。”今年,女儿已经1岁半了。第一次见面还是小婴儿,第二次回去,女儿已学会了走路。
王宇的老乡唐勇军39岁,当了21年兵。他的大儿子在读高一,理想是考军校,小儿子即将读三年级。在家时,唐勇军把时间几乎都用来陪伴孩子。
他也会和朋友聚会,但席间插不上话,反应也慢了。他察觉到,“只有和单位的人在一起才有话聊。”去年,培训结束后,王宇也在家待了两个月,但他很想回到单位,“马攸桥更像我的家乡。”
杨国强与王宇的情况有些相似。
他是马攸桥的副站长,35岁,甘肃张掖人。2017年,他从普兰机动队调入马攸桥。高海拔的生活令他的身体机能发生变化,他经常生病,被称作“药罐子”,冬天咳嗽有时会咳上两个月。
2021年,杨国强在食堂突感腹部疼痛,他忍着痛,满头都是虚汗。被送去阿里地区的医院检查后,才发现是肾结石。醒来时,他才发现手机里有妻子打来的四十多个未接电话。
尝试了两次外激光碎石无果,他被转移到拉萨,被下达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医生告诉他,一个大血包裹住了他的左侧肾脏,“再晚点,肾脏就要被摘除了”。
因为拉萨没有更好的手术条件,杨国强又被转院到成都,住了十来天。他至今感念上级曾对他说,“好好治疗,不管是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你的病治好。”
2022年4月,疗养结束,杨国强返回了马攸桥。支队希望杨国强调去低海拔地区,调养身体,但杨国强坚持要留下,“当时心里不知道咋想的,我就感觉马攸桥是我的家,是我工作这么多年来最有归属感的地方。”
这种归属感从何而来?杨国强认为,他们站岗执勤,能保障阿里地区的一片安宁山河。虽然海拔高,但是氛围好,很纯洁。每当他们救援一起车祸事故,或者是援助一些受困游客,心里面就会很充实。
18年来的高原生活,让王宇有了不少身体上的疾病。去年体检,他有肾结晶、干眼症、心室肥大、痛风等问题。但王宇说,他考虑过最坏的打算,也认为妻子和孩子会得到国家的照顾。“真有那一天,我会捐出我的器官,如果能对别人有用的话。”
【4】离别
一些改变仍在发生。如今,马攸桥建立了备勤用房,8月,还会建设一个光伏发电站。
7月6日,因总站实行高低海拔轮换,9名警察将要离开马攸桥。王金东、唐勇军、杨国强都在调离名单上。
在此之前,1996年出生的王金东被检查出了缺血灶。告别驻守了8年的马攸桥,他被调去山南市。他的妻子在那里工作,“这次也算夫妻团圆”。
唐勇军被调入了巴嘎乡,离马攸桥约130公里。那里海拔4600米,气候比马攸桥舒适一些。杨国强被调去扎西岗。去之前,他决定申请先回马攸桥,做一个正式的道别。
如今,王宇是在马攸桥驻扎最久的人,被叫作“王老兵”。他想起新兵分配时,曾被问到想去哪些地方。他的回答是,去艰苦的地方。他给自己设置了底线:“如果真的会走,我会争取最后一批离开,去一个差不多海拔的地方,继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最近,他回忆起上一次离开马攸桥的日子。2019年1月3日,他要出发去林芝报到。战友们给王宇践行,集体敬了军礼,他的眼泪控制不住。战友们给王宇传递了祝福:把身体养好,结个婚,再想回来就申请回来。
2020年,返回马攸桥之前,他在网上学习了更多的种植技巧,思考着回来后该种些什么绿植。
开春,王宇在阳光房的角落里开辟了一个小花池,种了20株百合。他在网上买了种子,用羊粪和土搅匀作了肥料。百合寓意纯洁和庄严的爱。他三天两头浇水,看着种子萌芽,长出叶子和茎。
百合冒了花苞。还有半个月,花就开了。
阳光房里的百合。图/九派新闻记者 肖洁
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编辑 任卓
【爆料】请联系记者微信:【【微信】】
【来源:九派新闻】
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