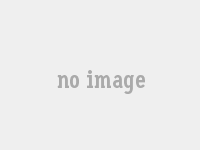褰掑娴峰唴鍏綊鏁呬埂
淘宝搜:【天降红包222】领超级红包,京东搜:【天降红包222】
淘宝互助,淘宝双11微信互助群关注公众号 【淘姐妹】
转自:人民政协报
人物名片: 张晓风,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华,江苏铜山人,8岁随家人赴中国*,先后就读于北一女中和屏东女中,毕业于*东吴大学。张晓风创作过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杂文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以散文最为著名,多篇作品入选大陆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她的作品在抒写家国情怀及社会世态中融入哲理。主要作品有《春之怀古》《地毯的那一端》《愁乡石》《我喜欢》等。
日前,*作家张晓风参访大陆,开启为期三天的文学交流活动。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与两岸文学青年对话,参访中国作协、十月文学院,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手稿……两岸作家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如何深化相互间的深厚友谊,在文学创作上相互激励,在新时期发挥文学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是参访途中她始终在与大陆文学界朋友、同道对话沟通的话题。参访期间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谈到她的文学观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对她的滋养。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看到鲁迅先生复原书屋时,感慨良多,可惜他早已离开了我们。拜现代医学所赐,我已经80多岁,比鲁迅先生长寿得多。也正因如此,我看到了中国土地的成长、人民的成长,而且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参与其中,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也激发我勤劳地持续写作。”已是耄耋之年的她,平时走路常拄拐杖,但在内心深处,她还是“靠文学‘靠山’滋养自己,心始终跟中国历史衔接,一生醉心于中华文化”的蓬勃创作者。
■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
共同的文化记忆
记者:故乡留给少年的您哪些印记?
张晓风:我祖籍江苏徐州,出生在浙江金华。父母告诉我,家乡那片土地一直比较贫瘠,粮食生产也不是很顺利,所以一直是一个比较穷苦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家的地也不多,所以我爷爷是靠教书为生的,教书也就是在乡下私塾里头教书。他教书的地方不在自己村子,而是在隔壁一个村子。有一次我回到老家,想看看爷爷教书的地方,有一个老人家跑出来,他说,你爷爷以前就是在我家吃饭的。我想,乡下孩子大概没什么钱,他说“你爷爷在我家吃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拿饭当作报酬,也可能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会给爷爷一点钱。总之,爷爷是用在当时很低的乡村老师的薪水,来养活一家人。
故乡留给我更多印记的,是我在南京居住的那段日子。那时候刚刚抗战胜利,大家从重庆搬回南京,需要大量的宿舍。在南京有个叫兰家庄的地方,盖了一大堆的宿舍,在那个时候算是豪宅吧,因为是两层楼的。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应该算是我有记忆开始第一个房子,还有一些从小到大居住过的房子,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中,或者只有模模糊糊的记忆。但对于兰家庄的房子,我会一直很怀念,会怀念我的小柜子,小柜子里的娃娃。这些年我还常常回南京,但是兰家庄已经不存在了,那些房子都被拆了。
记者:您在一篇散文中曾写道:“我有一个流浪漂泊的命运,但是很意外地在一个小小的岛上生存了很长时间,我的身体在*长大,可是我的心好像跟历史的中国衔接,不管是到南京或者是西安,我觉得都是我心灵的一个故乡。好像李白、杜甫、李商隐这些文学先辈,随时会跑出来与你相遇,所以不是地理上而是心灵上能跟传统衔接。”您心灵上与中华文化的天然联结,是怎么形成的?在大陆留下的这些记忆,会拉近心灵联结?
张晓风:应该说我的记忆比如说住的、吃的、人或者什么,这个只占一半,我大部分的记忆是从书里来的。就是说,读到书里所记载的古代以及现代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从阅读里面来的,可以说是文学给予心灵的滋养。所以,我希望能够把中华文化古典的东西充分地融化到现代生活里头来,而不是要弄得漂漂亮亮的古典来装饰我们。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确实蕴含了很好的精神,这个精神我们要了解,就像我讲的“菽水承欢”,菽不只是豆子,我们要想想豆子背后的意义。豆子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古人了解植物性的蛋白质对老人的好处,所以是一个有很美寓意的汉字,它蕴含了中华文化的孝道。
记者:所以您说“我舍不得不写字啊!”
张晓风:大家把汉字看成是交流工具,我觉得它比交流工具的功能还要多。因为汉字是有情感的,它是有画面感的,它所描述的东西能够透过画面文字来传递一些意象。所以,我总说,读汉字要读慢一点,慢慢地对每一个字留下来的意象,想一想,看一看。汉字所构成的词或者成语,这些都表达了相当丰富复杂且委婉的意蕴。我盼望着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汉字之美,同时汉字也是带领大家徜徉中华文化时光列车的一位“导赏者”,带领大家去解码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文化密码。
■能把中文说好实在是一个功德
记者:此前您提到苏东坡对您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张晓风:近一千年来的中国文人中,我认为最可贵、最值得去追随的一位文人,就是苏东坡。我们要将苏东坡介绍到全世界才对,因为这样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典范应该让更多人认识,他不单是文学好,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生活的态度也很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我从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5年从东吴大学去了一个叫阳明医学院的地方教书。很多人会好奇,去阳明医学院你教什么?都是医学生。其实医学生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还是要读中国文学,我就是给那里的医学生教中文。给医学生教中文和给中文系教中文会稍有不同之处,中文系学的内容会更细化、更专业,医学系就比较注重对文学本身的欣赏与体会,人家都说科普,实际也有一种文普,让文学普及化。他们将来不会做文学工作,但还是应该给他们多一点的文学教育。我从1975年到2006年,有30年在阳明医学院教书,阳明医学院后来扩大、和*交大合并了,更名成阳明大学,现在又更名成阳明交大。我这次参访北京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的校长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让我带来。现在阳明交大的校长是我之前的学生,他当年也是个文艺青年,他想和北京交大建立一个更亲密友好的关系。我教中文,喜欢古典文学,也希望古典文学可以影响他们作为医生对病人的、对人的一个观察角度。在我理解,中国文学其实是靠词语写成的,不是一个一个字,然而我们现在用词用得很粗糙,海峡两岸都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少再去念古书,写作要是注重行文,在白话文的基础上有一点文言的底子这样会比较好。
记者:阅读您散文和诗歌的读者与评论家,经常会提到“美感”这个词语,您的文字中又有婉约又有壮丽,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张晓风:就像生小孩,作者都希望生个漂亮的,作者也希望写出漂亮的作品。可是美在哪里?作者就需要去努力了,哪个东西是美的、好的,哪个东西是俗气的,要把他们分辨出来。能把中文说好实在是一个功德。往前追溯,好的语言其实是士大夫阶级在用,一般平民的语言也好,是小老百姓那种通俗的好,所谓上层社会和小老百姓的社会都在铸造某一种语言,那现在好像两种都式微了。士大夫那种优雅的、深奥的语言消失了,小老百姓也不太会讲谚语、歇后语,如果能够试着去恢复,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很需要好语言。广东话有谚语说“牵牛下水,六脚齐湿”,如果你牵一只牛去水里,要六个脚都一起湿,你别想让牛自己下水,人得把它拖着,那湿的就包括人自己的两只脚。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你如果是做领导的,你别奢望你的部下去做什么事,除非你自己走在前头。这不是什么大有学问的人说的话,但非常传神。过去不光是士大夫阶级有优美的语言,普通老百姓也有他们表情达意、很有哲理的语言,虽然这个语言有时候有点粗糙,可是很准确。我们现在的语言太简化,恨不得所有的问题都简化到yes or no这样的答案里就算了。其实在各个领域,好好地使用中文都是非常必要的,好的语言在任何地方都是重要的。
记者:海峡两岸文学界的交流一直很热络。您对两岸文学界特别是两岸青少年间的文学交流和两岸年轻创作者,有哪些建议呢?
张晓风:我觉得年轻写作者要找到一个“靠山”,这个“靠山”可以是古典文学,可以是外国文学。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找到一个特别的“靠山”,如果找不到,那就到民间去,去吸收、学习民间的智慧。创作者需要找到那个跟别人不同的“靠山”,有的人是平均靠,不过我觉得你要是想要有特色一点,还是要对某一个作家多下功夫,多去追随这个作家的作品,多读多学,“变心”了也没关系,再换一个好作家追随。
杩囧崍涓嶉楠嗗钩 杩囧崍涓嶉楠嗗钩灏忚闃呰
囧槑是什么意思,囧囧念什么字,囧囧这个字怎么读,囧这个字念什么?连续读罢骆平的长篇新作《半糖时刻》与短篇小说集《过午不食》,不由得想起李商隐那两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古人尚且珍重晚晴可贵,今人却往往忽略生命这最后的一缕认真。也许不能叫被动的忽略,而是主动的让位、隐忍,把恣肆与清欢留给青春一代,仅余自己享受孤独时光。除了“过”集里的《譬如朝露》《漫长的告别》两篇以外,其余三部/篇,均是以中年知识女性为主角,小说的叙述主视角也是中年女性,于是,在三部/篇小说里,女性的情绪起伏与幻灭感都在笼罩全篇。那是隐秘的、无法言说的中年,不再年轻,曾经燃烧过的激情在渐渐熄灭,可生命还不允许你停下,你的思绪、你的回忆、你对阳光的渴念,都在暗夜中折磨你、击打你、叫你反侧难眠。“半糖时刻”与“过午不食”两个词的中年隐喻意味那么明确又充满暧昧,犹如两个对临界点的提示,提示的不是女性“你该如何”,而是“怎样度过”。
两个作品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故事,但其实笼罩全篇的感受主体均是故事的女主角,“半”中的朱砂和“过”中的梁葵,两位中年知识女性对生活的观察态度与感受方式以强势姿态呈现出整个世界。她们都有仁柔而明智的个性,曾在青年时代自主选择了人生,已经活得无比清明却又无奈。
《半糖时刻》虽是长篇,故事线索倒也清晰,朱砂年轻时放弃了过去的家庭,选择新生活,也选择了新的伴侣。她曾为现在的丈夫罗勒(一个位高权重的学者)感动,但在20多年的相处中认清了他的面目,一个理性到近乎无情的男人。此刻朱砂对丈夫的爱夹杂了对强者的崇拜,也有对爱情逐渐平息的不甘。她心里还始终纠缠着对三岁便被自己事实上遗弃的儿子的歉疚,以及对过往曾为闺蜜现为亲子后母的青豆的复杂感情。就在这时候,丈夫的研究生斯羽,一个生于1995年的青年进入她的世界。
小说就是从斯羽和朱砂的邂逅写起,写朱砂对斯羽印象的逐渐改变,了解逐渐增多,好感与日俱增。小说带有明显的悬疑色彩,小小的生命谜题一个个揭开,读者很容易猜测最后朱砂要和斯羽发生点什么。的确发生了,但并不是言情的套路。丈夫虽然无情却豁达;也没有发生任何人对朱砂和斯羽恋情的指指戳戳;所有人好像都知道一点,又都出于各自立场表示理解和接受。最重要的是,小说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与斯羽的死去来结束,的确在情节上不可能再发展出什么“逆伦”故事来吸引读者眼球。
“半糖”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描述朱砂与丈夫的感情:“一切都是淡淡的,所谓的半糖状态。”这个词第二次出现是95后同事讲述对朱砂的印象:“您是半糖风格,有点甜,又不J,刚刚好呢。”“半糖”真是个无奈的说法,明明表面上中年的一切都如“半糖”般“恰到好处”,可心却像美式咖啡一样苦涩,对一个中年女性来说,“半糖”真的够吗?小说有一个淆乱中释然的结尾,“大家都是一边被生活虐得死去活来,一边紧紧看顾着自己的小命,兴兴头头地求取功名,繁衍生息。”可作者还是不忘添上反讽的这么一笔:“斯羽走在宝宝出生的那个凌晨,没来得及与朱砂说一声再见。”
短篇小说集中,《过午不食》篇幅只有《半糖时刻》的四分之一,讲了一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梁葵46岁了,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夫妇均是大学教师,丈夫还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儿子早婚,孙子刚刚降生,她却在丈夫的一次冲动之下怀孕了。
小说开头颇有张爱玲气息,一个躺在春日暖阳的旧躺椅里的慵懒女性,梦中遇见母亲,醒来省思着关于母亲的记忆。读者甚至一下子猜不到梁葵究竟多大年纪,直到婆母提醒她去为儿媳准备晚饭。梁葵得知自己怀孕后的感受是困惑迷乱的,她先后告知儿子和丈夫,得到的回答全是冷冰冰的,要为她联系产科大夫,把孩子打掉。倒是她曾深为厌恶的婆母支持她生下来。小说这一段梁葵的感受真是动人:“只有婆婆,让梁葵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真实的念头,那就是,她是多么想留下这个孩子。”当然没那么容易,丈夫可以被婆母说服,儿子身后却站着儿媳一大家。儿子长到二十多岁,还没立业就有了完整的家庭,自然不愿有人与他分家产。丈夫也怀着无法窥透的私心。在争执得一地鸡毛后,各方都得到了差强人意的结果,梁葵却发现自己腹中的胎儿两周前已经死亡。这是一个得到爱与期待都太少的胎儿,他/她还未降生便遭受到各方的恶意与不欢迎,于是他/她停止了在母亲体内的生长。这胎儿的死亡是否可以视作一个隐喻,那是梁葵生命激情的被压抑,全世界都反对她再次年轻,反对她至少再次做回一次母亲。
梁葵在小说最后想:“活过了中年,已然进入过午不食的状态……难以割舍的,不过是一份情怀罢了。而情怀,往往是最容易消散的。”她“想开”了,她经历得到胎儿死亡的消息后,第一去见的是婆母,那个已经过了十多年“过午不食”日子的老人,她搂着婆母――“抽泣着叫了一声:‘妈。’”这哪是什么与生活“和解”,不过是对环境的认命罢了。
《狻猊》的题材与以上两篇类似,很像村上春树《驾驶我的车》那般的探秘故事,写法也类似。村上那篇写的是一个丈夫在深爱的妻子死后,追根究底地探寻妻子出轨的秘密;而《狻猊》讲的是杜安静探究丈夫手机通信薄中给自己取名“狻猊”的原因。在探寻的过程中,杜安静那事业一路抬升、感情却死寂如灰的人生渐渐浮出水面。小说的写法很别致,杜安静和前情人老李对话的段落,冷峻而利落,颇有村上风味。说她写得像村上并不是说村上多么好,而是说作者完全可以在同一题材上流畅地驾驭另一种手法,不去依赖心理进展去铺开故事。
《譬如朝露》和《漫长的告别》两篇的题材则不同于前三者,“譬”是写一对笨拙而可爱的情侣不小心怀孕后发生的事,犹如猫打翻汤锅后的连锁反应,小情侣经历了一切酸辛磨难,看清了世相百态,各自得以成长。“譬”的写法是传统的写实,开头像极了《傲慢与偏见》:“恋爱闹到了一定的份儿上,不是结婚,就是分手”――这般口吻恰似后者开篇第一句:“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口吻同样地貌似世故而实则单纯。“漫”的故事更为独特,骆平在这篇里放弃她似乎惯用的女性视角,而是用一个男辅导员的角度去讲故事,一个未老先衰的疲惫男人,生活失去了朝气与未知。小说从一个女生莫名弃世写起,结尾“我”在梦醒之间仿佛见到那孩子,这段真是神来之笔:“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生前想要对我表达的,我从来就没有懂得,以后也不会懂得。”
孙犁在一篇文章里讲,写小说要尽量写熟悉的地方。骆平是个勤力的作家和学者,又是人到中年的女性,她对学院生活与女性生活大概最熟悉,也许因此两部书均是从此切入。在宏大叙事盛行的文学世代,她深描生命细节的创作选择可谓独树一帜。就像她在十多年前说过的那样:“终于有一日恍悟了某些真相,明白了生命绝非是一场可以自由操纵的棋局,输赢从来就是巨大的悬念。”我们且待她以自己对人生透辟的观察,写出更多有关生命悬念的故事。
作者丨张德强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