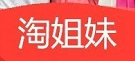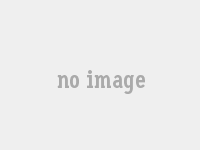证件照安卓版 智能证件照软件安卓
淘宝搜:【天降红包222】领超级红包,京东搜:【天降红包222】
淘宝互助,淘宝双11微信互助群关注公众号 【淘姐妹】
便民证件照是一款方便用户拍摄和打印证件照的手机应用软件。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功能和特色,帮助用户轻松地拍摄符合官方规定的证件照片。
软件功能包括自动检测和修复照片中的人脸,调整照片的亮度、对比度和色彩平衡,裁剪照片,以及添加背景和水印等。用户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证件照要求,选择合适的规格和尺寸,如身份证、护照、学生证等,便于打印和使用。
软件的特色在于它提供了专业的证件照拍摄指导,包括照片的合格标准和拍摄的技巧。它还提供了一些特殊效果,如美颜和滤镜,让用户能够自己调整和美化照片。
软件的内容包括各种不同版本的证件照模板,以及相应的要求和规格。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模板,并进行个性化的调整和编辑。
软件评测显示,便民证件照在照片处理和打印方面表现出色。它能够根据不同的证件要求,自动检测和调整照片,确保照片的合格性。同时,软件的操作界面简洁直观,功能易于使用,适合初学者和普通用户使用。
软件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便利的服务。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手机拍摄和编辑证件照,无需前往摄影馆或专业机构。此外,软件支持照片的在线打印和快递服务,方便用户收到他们所需的证件照片。
总之,便民证件照是一款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帮助用户实现方便快捷的证件照拍摄和打印。它的特色、内容、评测和优势都彰显了它在证件照领域的出众表现。
100张杭州老照片 100幅杭州老照片
100张杭州身份证图片,杭州百年老照片,杭州百年小吃,杭州图案沈弘其人
沈弘,杭州人,北大第一位英语博士生,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沈弘教授遍访哈佛、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国内外难得一见的珍贵图文资料,整理、编译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记录,意外地成了杭州乃至中国老照片的收藏者。
沈弘发现的这些老外拍摄的老照片,再现了处在民国初年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百象。尤其珍贵的是,这些杭州和西湖老照片,不仅时间较早,而且景点最为齐全。像费佩德在1910年左右拍摄的西湖景点照片就包括西湖全景图、宝石山、保m塔、大佛寺、北高峰、六和塔、玉皇山顶七星缸、城隍山等等,大多为国人第一次所见。
20世纪初期从小瀛洲看雷峰塔 拍摄者:甘博、图片提供:沈弘
20世纪初期的之江大学操场 拍摄者:甘博、图片提供:沈弘
2007年夏天,浙江大学教授沈弘在*辅仁大学图书馆,第一次发现了蕙兰中学(杭二中前身)的外籍校长葛烈腾所写的回忆录――《人间世》(Hea【【微信】】)。
这本后来被称为“杭州版《拉贝日记》”的书中,清晰地记录着他在二战期间亲历的炼狱景象: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人间天堂”之下,“面无血色、腹部水肿的孩童沿街乞讨;受日本兵追赶的妇女发疯似地逃上屋顶,我们都能听到附近瓦片震动的声音;还有一些人蜷缩在门道口静静死去……”
四年时间里,葛烈腾与蕙兰中学坚守杭城、救死扶伤,庇护了近两千名孤儿与数千名妇女,拯救了数以万计的难民。
葛烈腾校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生命的实现取决于对物质的掌握,那实在是很失败的事。
不,生命鲜活的价值,更在于无形的付出,
比如认真工作,减缓民众饥饿和疼痛,将理想带给那些需要靠一种信念去顽强生活的人们,给需要的人带去同情和慰藉,通过鼓舞的文字将希望与勇气带给那些正承担重压的人、那些需要救济和帮助的人。”
《人间世》一书中留存的避难所照片,此书去年10月浙江古籍出过新版。
为之动容的沈弘顺藤摸瓜,在葛烈腾的母校(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档案馆里找到了他在1938年和1941年寄往美国的两封长信,信中详细讲述了他在杭州救济难民的困难,和日军在杭所犯的暴行。
沈弘将其仔细翻译并公之于众,杭州人的心随之震颤。此后几年,这个曾经陌生的洋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2017年,为了传达一句来自杭州的谢谢,沈弘开始找寻葛烈腾先生的后人。他在美国家谱网,写了给美国网友的一封信,讲述葛烈腾夫妇的事迹。信发出后,许多美国网友义务帮忙,在网上接力寻找其后代。终于在次年年初找到了葛烈腾的孙女。
▲2017年12月29日,沈弘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网友的邮件,信中写道,葛烈腾的直系亲属找到了,葛烈腾的孙女还活着。 图片提供:沈弘
或许在沈弘成为北大第一位英语系博士生、潜心笃志研究中古英语时,他并没有料到30年后,自己竟会站在东西方的交叉口,打捞时间,同时为杭州留下别具一格的书香。
他从丹麦建筑师艾术华在1937年所写的关于保m塔的研究论文里,捞出了保m塔建造之初的内塔核心。百年时光,仿佛只在一伸手间,你便能触到斑驳脱落的塔墙之下的肌肤。
保m塔外墙脱落露出的内塔 图片提供:沈弘
他从1915年美国女诗人吉利兰的西湖蜜月旅行里,捞出深藏湖心的英文西湖风景诗:“三个月亮颤颤巍巍”,“湖底精灵窃窃私语” 。古典西湖之美,顺着那一汪天然的诗性底蕴,从苏东坡流向吉利兰,从一种语言流向另一种语言。西湖是没有理由的,只要在场,诗意自然发生。
美国的东亚艺术史学者马尔智所摄的三潭印月 图片提供:沈弘
那些老杭城的市井日常也好,那些旧人间的山河永寂也罢,从西方人的记载里浮上水面,又通过他的翻译转述和考证研究,慢慢打捞出水,而今渐渐“大白于天下”。
至今,他已编译撰写了超过四十卷相关书籍,依然孜孜不倦,为杭州留下珍贵的图文读本。他是沈弘。
“爱德华・库克曾是一名军官,而如今,他进了监狱。日子一天一天,于他并无二样......”那盘磁带播讲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
故事的题目叫《逃亡者》(The Man who Escaped),讲的是一个英国特工逃脱敌人追捕的故事。
时隔十多年之后,当沈弘来到大洋彼岸的牛津留学,在高桌晚宴上遇见一个伦敦金融中心的警察总监,听到许多苏格兰场的内幕故事时,他仿佛终于见到了曾经在故事里生活的人。
时间再往前倒转。大一那年,每个周末,沈弘几乎都会与军官“库克先生”一起度过――这是系里上课专用的一盘听力磁带,跟烙饼一般大。
那会儿沈弘已经23岁了,好在1977年的北大新生里,他不算太老。一个宿舍共用一台老式开盘录音机,一到洗衣时间,沈弘总要耐着性子绕好磁带,边洗边听。一年后库克先生的故事,老沈早已烂熟于心。
哪儿是励志刻苦啊,老沈那是久旱逢甘露,饥渴得很。
沈弘是个读书人,偏生撞上了读不到书的年代。
作为“*”第一批高中生,沈弘毕业后原本留在杭十中任教,一纸通文又下到工厂锻炼,成了西湖伞厂的一名工人。
父母都是英语教师,家里的英语小说,成了沈弘自学英语的开始。雨果、狄更斯......后来,他读到了哈代的
《无名的裘德》
。裘德是个农民,住在牛津附近,一心想去读牛津大学。于是他自学拉丁语,终于有机会进城,参观了牛津大学。
“他的身世和当时的我,如出一辙。”小说看得人心颤,沈弘就是那个向往北大的伞厂工人。
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
待到机会来临,自然如饥似渴。以至于同寝室小伙子们一度打趣,质疑他是否还有七情六欲。问急了,沈弘也会一本正经地回答:
“人有的感情我都有。
”据说是马克思的名言。
在北大同学记忆里,沈弘读书之刻苦,堪比苦行僧。殊不知当时的他,便是那一叶初泡的龙井茶,在翻滚的腾腾水气里渐渐舒展开来。
沈弘在北大未名湖前留影 图片提供:沈弘
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善本书,是在1990年。那会儿他刚从牛津访学归来,回到母校任教,开了一门“西文目录学和版本研究”的课。集合了燕京、中法、中德学社等诸多学校资源的西文善本书库,不少书堆在橱窗里,解放后便没人管了。书库里满满的宝藏,却披上了一袭厚厚的尘土。
一来这些书大部分用拉丁语写就,参杂法语、德语、葡萄牙语等多语种书籍,当时能看懂的人很少。二来整理大量古老陈旧的书籍,即使在图书馆管理者看来,也是个枯燥繁琐的工作。
语言也不全懂,沈弘却觉得自己打开了宝库里的新世界,每一日都像在探险,随便一翻都是宝贝。
也是这时候,他第一次从外文书里,看到了旧时的杭州模样。
那是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来自美国传教士来恩赐(David N. Lyon)的《1870年杭州日记》(Hangchow Journal 1870),讲述100多年以前,皮市街(现皮市巷)的市井人生。从小在那附近长大,那是沈弘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异国视角的讲述下,又给了他另一种陌生而新奇的感受。
花了大半年时间,沈弘把这2000多本西文善本书逐一整理翻阅,终于完成了图书馆交付的任务,发表了一篇关于馆藏两千多本西文善本书内容及评价的报告,在《北京大学学报》上。
明白问题,才会知道答案的意义。
1999年的某一天,一个学生急急忙忙跑来沈弘这儿报告,说学校操场角落的地摊上,居然在贱卖京师大学堂的书,几块钱一本。
沈弘便知事情不对。来来去去一问才知,这上百本价值惊人的旧书,正是从北大图书馆流出去的――图书管理员不知其价值,直接当作废纸卖了。
看书是一种能力,爱书更是。沈弘赶紧找到图书馆馆长,一番苦口婆心,你看我辛辛苦苦费了半天,才从里面找出一两本,回头一看外面,竟然大量贱卖,你说我看得下去吗? 馆长这才下令,把这些书全部收回。
其实此前两年,他便已发现这个问题。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筹备时,沈弘第二次从哈佛访学归来,再次受托整理图书馆的西文书。意外的是,他早前在书中见过的老照片,居然已经被人撕去不少。为此,馆方配备扫描仪,请沈弘将其中的照片转成电子版保存。
就这样,馆里积累了一批清末民初的照片,2000年办了老照片展览,惊着了不少历史系老教授。这些老先生一辈子在这儿意裂芯浚不知身边方圆之地,就有这么好的照片。
上世纪80年代,博士属于稀缺物种,沈弘更是北大英语系的第一位博士生,轻易不可放出国门,原本联系好了赴美访学,临时告吹。
死心是不可能死心的,这辈子都不会。恰逢其时,导师李赋宁在美国碰到了
牛津学者布鲁斯・米切尔
,古英语界的元老。由此取得联系,沈弘终于在1988年带着国家奖学金,第一次出国访学,拜入布鲁斯・米切尔教授门下,日日夜夜泡在牛津的图书馆里。
可你若以为读书人就木讷,便错了。沈弘买书,自然也有买书的门道。周末就去书摊或教会慈善书店里淘旧书,这些地方特别便宜,挑出好的,转手卖给收购旧书的书店。靠这样的差价,最后没有花钱,带回了几百本好书。
一年后,沈弘回到北大,开了一门课程,叫“西文目录学和版本研究”。这是牛津的基础课。研究文学手稿,必须了解一本书诞生的过程,用的是什么纸、是如何印刷......“以塞缪尔・理查逊为例,他是小说家,也是印刷商。有时他对自己的小说不满意,每次出版都会修改内容,前前后后改了十几次。”
首先搞明白了哪一版最佳,然后才能分辨书的价值。每到一个地方,沈弘都要去逛逛当地的旧书坊,有时5美元就能买到很好的旧书。
▲Book Barn(旧书库)是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卖旧书的著名小镇岛。镇上有十几个书店,街边也有书摊,距离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大约八英里,很多中国访问学者专程去那儿买书。 图片提供:沈弘
他曾在布达佩斯的旧书店里,遇见一本来自1566年的书,拉丁文,羊皮纸,写的是宗教历史,书口还带着刻花的金属扣,至今保存完好。沈弘爱不释手,花了大约1000元人民币,把他带回了家。
来自1566年的书 ?城市秘密
他曾在塞纳河边的书摊上,发现了一批牛皮旧书,随便一翻就有200多年的历史。1754年出版的《堂・吉诃德》,才花了几十法郎。
他也曾在丹麦哥本哈根一家即将关门的书店里,买到了最后一批打包出售的旧书,100多年的历史,封面里的藏书票还完完整整,只要两三块钱人民币一本。
100多年历史的书里,藏书票依然崭新如初。 ?城市秘密
还有一回,他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附近的镇上闲逛,看见一家旧书店,就走进去问店员,有没有跟中国相关的书籍。店员找了半天,拿出一本书,书名是
《新旧中国:来华三十年的个人回忆和观察》,
打开一翻,便看到了六和塔重修前的老照片。
沈弘一眼认出了这本书。他曾在北大的图书馆里见过,作者名叫慕雅德,是曾在杭州生活过的一位传教士。他用中英文双语撰写了许多作品,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在华生活。
1865年,他从宁波来到杭州,走的是水路,一路上的经历让他大开眼界。当他即将到达目的地时,书中这样写道:
“在渡船快要到达码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句中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点没错,在这个温暖的初夏午后,我从远处t望杭州,真的就像是窥见了天堂的一角。”
沈弘收藏的《新旧中国:来华三十年的个人回忆和观察》 ?城市秘密
六和塔重修前的模样 图片提供:沈弘
店员报价20英镑,沈弘听来觉得贵了些,便犹豫了。离开后越想越懊悔,又特地转回去,还是买了下来。
后来,沈弘这样形容慕雅德:“依仗其非同寻常的语言表达能力,使自己成为了沟通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一座桥梁。”而老沈在做的,何尝不是同一件事。
在
《城记・杭州:1793-1937遗失在西方的杭州记忆》
等书中,沈弘记录了他在图书馆角落里,遇见的形形色色的“白皮肤杭州人”。
2019年底,沈弘所著《城记・杭州:1793-1937遗失在西方的杭州记忆》出版
他逐渐养成习惯,每到一处,遇见一人,总要问问,有关于中国的书吗?有杭州的老照片吗?
1793年第一个为后人留下西湖写生画的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1796年举办西湖风景画展的荷兰大班范罢览、1915年蜜月旅行中写下西湖风景诗的美国女诗人吉利兰、1936年写下《论杭州保m塔的建造历史》的丹麦建筑师艾术华......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特使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笔下,杭州城外的运河和寺院。 图片提供:沈弘
1907年,英国画家李通和在断桥所绘的西湖水彩画。 图片提供:沈弘
几乎每一段寻找和发现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2012年,沈弘与美国塔夫脱总统的后人合著《看东方:1905年美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之行揭秘》。偶然聊起发现,这位塔夫脱的一位朋友,正是甘博的外孙。
如今我们看到的大量民国旧照,都是这位
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
拍摄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照片的存在都鲜为人知。直到1984年,甘博的女儿在家中一只鞋盒里,发现了一大批玻璃底片的相片,出自早已过世的父亲之手。
在塔夫脱的连线下,沈弘与甘博家族的后人们日渐熟识,并受其委托,将1908年甘博一家来华所摄的杭州旧照,编撰出版成
《西湖百象――美国传教士甘博民国初年拍摄的杭州老照片》
一书。2016年,沈弘去美国时,还专门去看望了在纽约大都会艺术馆里做研究员的甘博外孙女。
沈弘与甘博的外孙女 图片提供:沈弘
甘博的好友,
美国传教士费佩德
,与寻觅者沈弘,也发生了一段有趣的邂逅。
费佩德曾是之江大学校长,在华生活五十余年,直到1945年才离开。他撰写的
《杭州―浙江游记》
(Hangchow-Chejiang Itineraries)是外国人来华的必读书目。
沈弘在北大图书馆里见过他拍的部分杭州老照片,便在网上寻找他的后人。2006年,沈弘调任浙大,一个偶然的机会联系上了费佩德的堂侄。堂侄便将费佩德外孙的邮箱给了沈弘。
《杭州―浙江游记》(Hangchow-Chejiang Itineraries)
外孙罗伊・休厄尔对外祖父所知甚少,也从未到过中国。只是从小耳濡目染地听母亲珍妮特说起那个远处的“故乡”杭州――她在西湖边出生长大,在西泠印社学习书法和绘画,在浙江大学的小教堂里订婚,“直到她晚年撰写回忆录时,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杭州人,尽管她的杭州话在自己家里已经没人能够听得懂了。”
外祖父过世后,将1000多张照片留给了他,他便一直压在箱底,没有仔细研究过。好在罗伊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底片一直保存完好。直到三十多年后,一封来自中国的邮件,重新打开了这段封藏已久的往事。
2007年,罗伊在沈弘的邀请下来到杭州,带来了外祖父的1000多张中国老照片。顺着外祖父《杭州―浙江游记》中的5条游览路线一一走过,还去了母亲回忆录里提到的地方。
2007年,顺着祖父费佩德的路线,罗伊・休厄尔夫妇与沈弘一同游西湖。图片提供:沈弘
但事实上,这千余张照片里,真正属于杭州影像的,只有100张左右。而辨识梳理的过程是漫长而繁复的,许多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都难以辨认。
对着照片,沈弘带着两个研究生学生,一一确认方位。为此,沈弘还请教了许多专家,包括杭州老房子专家仲向平。有时候,尽管照片所注为杭州,但谁都无法确认其所在,最终还是被剔除。
以费佩德一家在湖滨附近的住址为例。上世纪初,之江大学新校区造好后,他们一家还曾专门买了块空地盖私宅。建成后,据说成为当时杭州内城里最高的一座楼,有三层。一楼是教会活动场地,二楼以上就是费佩德一家住宅。这栋标志性建筑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拆毁了。
费佩德杭州老家的过去与现在 ?城市秘密
为了分辨这个地方,沈弘和学生四处询问,最后,通过思澄堂的牧师,找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教友,这才终于认出,照片里的老家,就是现在的工人文化宫位置。
2009年,总算厘清了老照片中所包含的100余张旧时杭州影像,沈弘与罗伊合作举办了一场老照片展览。随后,两人合作出版了
《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德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
。
沈弘、罗伊・休厄尔合著《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德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
在费佩德家族的往事里,沈弘原本是个讲述者,是个介绍人,却没想到冥冥之中,他自己,竟站在故事的另一端。某一刻,故事也会同他的人生产生交集。
罗伊提供的老照片里,有一张1908年育英书院全体师生在校园里的合影。大家坐在小操场上,背后几幢教学小楼,校园内视野开阔。很久之后,沈弘才知道,这个校园,就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
1908年育英书院全体师生在校园里的合影 图片提供:沈弘
育英书院,是浙江第一所新式高等学府。1911年学校从大塔儿巷搬到钱塘江边,成了后来的之江大学。原本大塔儿巷的校址,后来成为了杭州正则学校的校园。
到了1947年,正则学校迎来了一位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的年轻教师,不久后成为校长。他就是沈亨寿先生,沈弘的父亲。他们一家,当时就住在这个学校里。
几经变迁,门牌从大塔儿巷19号,变到了大塔儿巷8号,又变成了今天的大塔儿巷15号。好在内核始终未变,今天,它的名字是杭州退休干部(职工)大学。
大塔儿巷15号现状 ?城市秘密
上世纪90年代,沈弘曾在北大开过一门课,以老照片为主,重看历史的AB面。可要看懂一张图,却并非易事。将图像作为重要一手史料,从另一面阅读历史,沈弘一直是“图像证史”的先行者。
去布里斯托尔大学是在2003年,沈弘本来冲着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去的,到了那儿却临时调转枪头,花了整整半年时间泡在大学图书馆的书库顶楼里――沈弘发现了一整堵墙数百卷的
《伦敦新闻画报》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这个以图画为主的英国周刊,自1842年创始之初,就开始派遣画师和记者赴华,因而记载了大量中国近代的第一手现场图像资料。
伦敦特派画家在中国画速写,刊于1857年7月18日《伦敦新闻画报》。
西方记者所报道的内容和视角,很多时候和我们惯常的史料观点不同。细细看罢后,沈弘一心想将这里面的中国旧事转达给更多人听。17年间,他翻译撰写了上百篇文章,其中翻译之困难,连他这位专家都始料未及。
举个例子,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攻打广州,从香港沿珠江上来,期间经过了上百个军事炮台,和水系密布的珠江支流。这些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专有名词,如今要想重新翻译成中文,却远比想象的要麻烦。
我们当时的地图里往往没有细致地标注支流,100年过去后名称变化自然也很大。而除了少数现在被开发成旅游景点的炮台之外,其他更是难以自行考证。为此沈弘也咨询了不少相关人士,显然,涉及军事相关问题的公开,总还是让人有所顾虑。
信息量之大,沈弘一度想放弃。后来又有一位出版编辑找来,希望沈弘编译《伦敦新闻画报》的内容。沈弘最终还是咬咬牙,做了下来。由此集结出版的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
,目前已出版7册,仍有许多内容未完成。
沈弘编译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
1991年,沈弘来到美国哈佛大学英语系访学,为了挣学费,他先是跑到美术图书馆里打了一年工,找书理书、打扫卫生,后又去法学图书馆干了三年出纳,几年下来,把图书馆的书都翻了一遍。
沈弘在哈佛商学院图书馆(Baker Library)找书 图片提供:沈弘
“在国外,图书馆是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
且不论国内图书馆整理的水平,进去时常像进了迷宫,许多珍贵的资料,没有放进对的人手里,就这么扔在无人知晓的书库角落里发霉。
单说开放性这点,国内一比到底还有差距。“国内的图书馆,有时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比如有一批书,从调任浙大那年,沈弘就申请查阅。馆内管理者回复他,“这个我们要研究研究,看能不能拿出来借阅。”研究到现在,沈弘一等就是十几年。
这也是为什么沈弘每年还是更愿意将大量时间花在国外的图书馆里。
▲沈弘的部分借书证。除了哈佛和牛津,耶鲁大学、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丹麦皇家图书馆、多伦多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图书馆,都有很多与中国相关的收藏,都留下过沈弘的足迹。 ?城市秘密
最近,沈弘工作室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准备在德国摄影师海达尔・莫里森留存的17000张照片中选出2000张,按照6个不同题材,编撰成一套丛书。第一本已经编写好了,主题是
“老北京的葬礼与婚礼”,
其中包含着很多民国时期北京的葬礼旧习俗,可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震撼画面。
直到现在,沈弘编译出版的书籍已超过50册。
他的电脑里,还存着数以千计的时间地点和文脉故事尚未厘清的老照片,而当他看到尚未重浮于世的老照片,新的研究寻觅便列入了日程。
掘书人沈弘,从未停下,全世界漂泊,不停地找书,不停地看书,不停地出书,而所有努力都在向着一个方向:故乡。他的故乡藏在书香里。
沈弘发表的部分作品 ?城市秘密
沈弘家有个阁楼。木头楼梯往上走,满满几列“通天”书架,恍然间好似走进了某个图书馆。在他的书架上,多是我们看不懂的外文书。英语、拉丁语、法语、德语,
沈弘是世界的读者
。“他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浪’,天涯海角,最后‘流浪’到中国,到故乡杭州。”
阁楼里书声回响,其中许多书都生僻冷门。它们曾在置物架上,曾在书库旮旯的落尘中,曾在街边的地摊上,无人问津。可有一日,它们遇到了领悟意义的人,找到了它们的读者,于是便不再“平平无奇”。
沈弘的书房 ?城市秘密
推荐书单:沈弘著/译作
《城记・杭州:1793-1937遗失在西方的杭州记忆》
《西湖百象――美国传教士甘博民国初年拍摄的杭州老照片》
《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德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
《佛法之渊/灵隐文丛 : 近代杭州寺庙旧影》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 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
《寻访1906-1909 : 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
《晚清映像 : 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